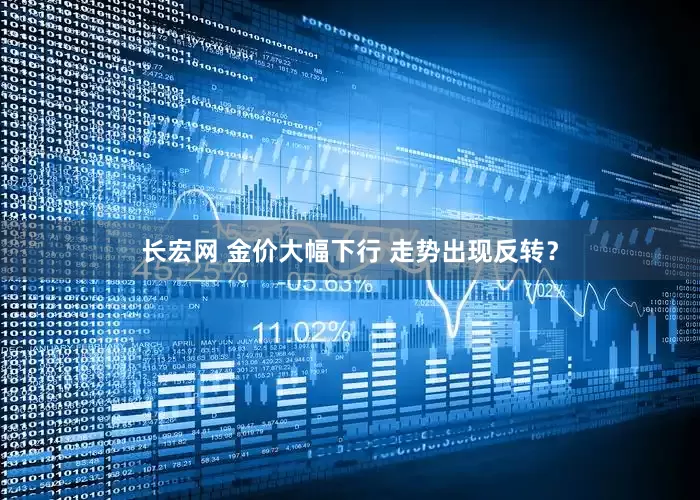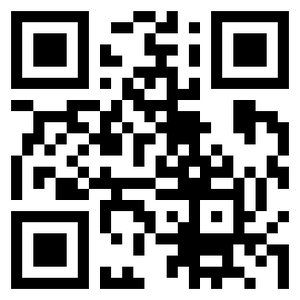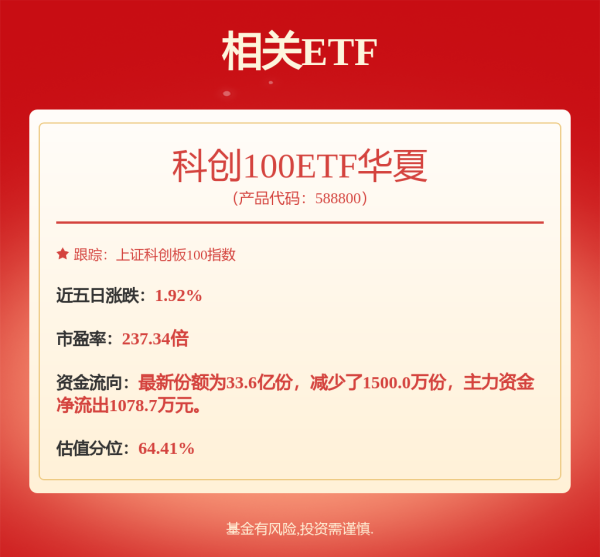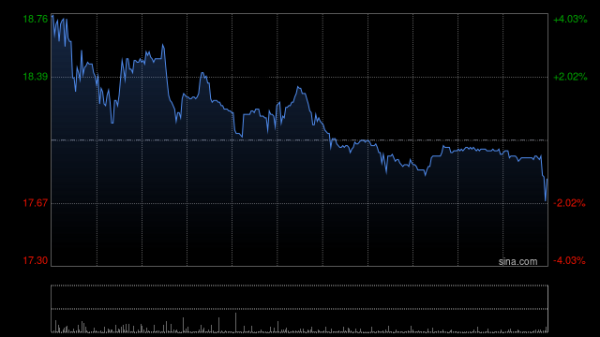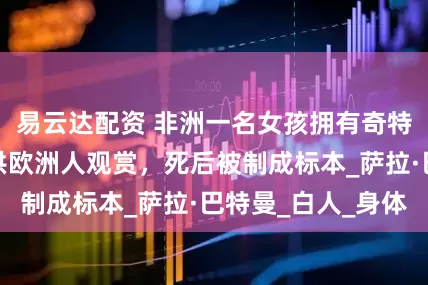
1814年易云达配资,巴黎街头出现了一位异样的少女,她全身赤裸,棕色的肌肤暴露无遗,被关在一个狭小的兽笼里。面对身穿华丽服饰的围观群众,她显得格外羞涩与不安。那个小小的笼子将她紧紧束缚在有限的空间中,她无助地望着那些嘲笑她的人们。
围观的人们一边大声嘲弄她过于肥大的臀部,一边用折扇遮掩口鼻,仿佛这样可以掩盖他们的恶毒言辞,给自己留下一点所谓的“高尚人格”。人群不断更替,换了一拨又一拨,最终散去,一个白人男子拖着那个装着少女的兽笼,继续带她走向另一个街区。
每当少女因饥饿或痛苦哀嚎时,她都会遭到白人的毒打。整日走街串巷,她只能获得像猪食一样的糟糕饭菜。然而,她绝不会想到,她的悲惨命运远远超出了眼前的苦难。
这名黑人少女名叫萨拉·巴特曼,1789年出生于非洲好望角一个叫科伊桑的小部落。十八世纪对欧洲和非洲来说意义迥异:对欧洲而言,这是一段历史性的发展时期,工业革命推动国家实力飞速增强,殖民扩张成为强权标志。
展开剩余84%然而,对非洲来说,十八世纪则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欧洲列强的侵略如猛兽般撕裂这片大陆,无数黑人沦为商品和奴隶。在战争和瘟疫的双重打击下,许多非洲人甚至连活着都变成了奢望。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巴特曼的存在充满了不幸,而她更加跌宕起伏的命运则源于她独特的体态。科伊桑部落里,女性以肥大而坚实的臀部和强壮的臂膀为美,而巴特曼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对于原始部落社会来说,女性的生育能力与身体特征直接关联着美的标准,因此在欧洲人到来前,她在部落中被视为美丽的象征。
但对白人来说,这样的身体特征被视为“野蛮”和“未开化”的标志,是他们种族优越论下的“落后”象征。非洲黑人在他们眼中,始终被贬低为非人类的存在。巴特曼原以为自己的命运已经够苦,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身体竟成了她未来深重灾难的根源。
1810年,一艘欧洲货船驶入好望角,船员们除了搬运货物外,还在觊觎南非原住民。英国外科医生邓洛普和荷兰奴隶主的哥哥德里克一眼便看中了巴特曼的“特别”之处。
看到她的瞬间,这两个冷血白人仿佛已经预见了未来的财富滚滚而来。他们坚信易云达配资,这样一个怪异的“奇观”带到欧洲,必将掀起轩然大波。
为了诱骗巴特曼跟他们回欧洲,两人许诺了奴隶最渴望的自由和财富。对于身处奴役深渊的巴特曼来说,这无疑是天赐的机会。她几乎未加思索,便跟随两个陌生的白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然而,邓洛普和德里克并未兑现承诺。巴特曼踏上欧洲大陆后,两人的真面目逐渐暴露,温言软语变为残酷剥削。
他们将巴特曼关进铁笼,像训练野兽般鞭打她,逼她做出猿猴般的表演。饮食极其匮乏,为了制造噱头,残忍的两人甚至剥去她的衣物,在宣传中刻意强调她“异乎寻常”的体态。
经过几日“训练”,两人认为时机成熟,便带着装着巴特曼的兽笼来到广场公开展览。彼时,欧洲人对非洲种族了解甚少,见到赤裸的巴特曼时,他们的虚伪面具顿时瓦解,爆发出一阵阵疯狂的喝彩。
曾自诩为绅士淑女的观众,竟在街头公然讨论这位手无寸铁女子的身体,甚至有人趁机对她动手动脚,但他们心中只有动物,而非人类的尊严。观众的欢呼愈盛,德里克和邓洛普的钱包便越鼓,利益驱使着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此后,二人带着巴特曼巡回演出,为了取悦白人观众的优越感,竟将羽毛粘贴在她身上,羞辱她的非洲身份。
巴特曼就在这种悲惨的生活中度过了四年,走遍了英国的各个角落。随着媒体报道易云达配资,她被冠以“畸形人种”的名号,最初的轰动逐渐消退。利益枯竭后,德里克和邓洛普便将她卖往法国,意图在新国家再度开启展览。
不久,法国观众对巴特曼的兴趣也日渐冷淡。德里克和邓洛普不愿再花费心力,便将她卖给了动物驯养员。从此,巴特曼的生活更加凄惨。她每天忍受驯养员的鞭打,和动物们同吃同住,被关在兽笼里,随时被运往不同地点展览。
可怜的巴特曼最终不堪忍受这种非人待遇,在某个清晨虚弱倒地,再未醒来。
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那么巴特曼终获了她梦寐以求的安宁。但令人发指的是,贪婪的商人并未满足于她的死亡,他们对她的尸体做出了更加残酷的事情。
她的遗体被卖到实验室,成为研究的对象。科学家们解剖她的身体,用她的血液做多次化验,将她的身体制成各种大小的模型供展览。
事实上,那些自称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专家”根本没将巴特曼当作一个完整的人类,他们的行为犹如一场荒谬的游戏,目的仅是证明白人高贵、黑人卑贱的种族论调。披着科学外衣的结论换来了他们的荣誉和金钱,而唯一的受害者只有巴特曼。
研究成果发表后,巴特曼的身体依旧无法安息。她的头颅和臀部被浸泡在福尔马林中,成为博物馆中的标本。她大概未曾想过,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无法逃脱被人观赏的命运,这样的羞辱竟持续了两百多年。
两百多年间,世事变迁,奴隶制逐渐瓦解,被压迫的人民开始觉醒和反抗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再横行无忌的今天,反对种族歧视的声音日益高涨。巴黎的人类博物馆因展出巴特曼标本,频遭批评。
对非洲人来说,巴特曼不仅是个人,更代表着整个受屈辱的黑色人种。她生前所遭受的委屈,映射出黑人的历史痛苦和压迫。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人类博物馆被迫撤下巴特曼的遗体展览,但并未正式道歉或归还遗体。
非洲国家长期为此奔走呼吁,要求将巴特曼遗体送回非洲安葬。法国博物馆却一直未作回应。专家认为,博物馆的态度并非因巴特曼遗体珍贵,而是因为馆内还藏有大量其他人类遗骸。
如果归还巴特曼,是否也得归还古埃及木乃伊、新疆戈壁干尸?对博物馆而言,这意味着重大损失,因此他们拒绝妥协。
然而他们忽视了,巴特曼的遗体不同于无名木乃伊或干尸,她有明确的身份和名字,是活生生的人类。不归还遗体,无异于剥夺她作为人的尊严,这对非洲人民来说是另一重侮辱。
事件长期僵持,巴特曼始终未能回家。尽管如此,非洲人民未曾放弃争取。随着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黑人地位提升,巴特曼回归之事重新被提上议程。
可惜曼德拉毕生努力未果,将任务交予继任者姆贝基。姆贝基经过七年不懈努力,终于让此事露出曙光。
2002年,在非洲黑色人种的共同努力下,巴特曼的遗体最终回到了好望角,人民为她举行了盛大葬礼,期盼她的灵魂能够安息于故土。
至此,巴特曼经历了两百多年悲惨命运易云达配资,终于画上句号。这也象征着被奴役非洲黑人苦难的终结,未来不再有任何有色人种因身体特征而遭受折磨与羞辱。
发布于:天津市点石策略通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